朱述道的青春与情书
初见朱述道时,86岁的老人正坐在葡萄架下翻看着一本泛黄的手写稿,说起60多年前初到新疆的日子,眼角的皱纹里都盛着光。
“当时就想着国家需要人,咱年轻,就该去闯闯。”他不会想到,这场始于“响应号召”的远行,会变成60多年的扎根;那些没来得及写给家乡的信,会化作6万字的手写回忆录,字里行间全是天山的风、麦浪的香,和一个叫王翠霞的姑娘。
1959年,20岁的朱述道和4000名支边青年,从江苏徐州挤上火车,一路向西。到新星市柳树泉农场那天,迎接他的是漫天黄沙,住的是半地下的地窝子。140个来自江苏、上海的青年挤在这一间地窝子,铺盖挨着铺盖,夜里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和窗外的风声。
“苦是真苦,但没人喊退。”朱述道记得,白天大家扛着十字镐往天山脚下走,要挖一条40多公里的渠,磨破了手,裹块布条接着干。他总在夜里琢磨省力的法子,在地上画渠线、算坡度……“咱不能蛮干,得让力气用在点子上。”
1961年,朱述道当上生产队长,他较真的劲儿更足了。农场种子站要求一亩地播5公斤种子,他却蹲在地里较上了劲。带着尺子量行距,数着玉米粒试播,最后拍板:“2公斤刚好,密了反而抢养分,长不好。”有人笑他是“书生胡闹”,他就守着试验田不挪窝,从出苗到拔节天天盯着。
等到秋收,他的地块产出的玉米不仅棒大粒满,每年还能节省900多斤种粮。“那可是100个娃娃一个月的口粮啊。”朱述道拍着大腿,眼里亮闪闪的。
在苦日子的缝隙里,生活的甜却藏在了定西车站的匆匆一瞥里。1959年11月,火车在甘肃定西站停靠时,朱述道在站台散步,一个穿蓝布衫的姑娘从身边走过,梳着两条麻花辫。
“大眼睛,精神得很”,他心里一动,没敢打招呼。没想到一个多月后,在同批支边青年付荣太的婚礼上,这姑娘竟是伴娘。
她叫王翠霞,和他同是睢宁老乡。那天朱述道当主持人,故意把新娘“24岁”念成“42岁”,逗得全场大笑。他瞥见王翠霞捂着嘴笑,眉眼弯弯的,他心里的种子也悄悄发了芽。
后来,农四连到农一连的七八公里土路,成了他的“爱情专线”。王翠霞总把省下来的白面馒头包在布里给他,给他补衣服的针脚比供销社的还匀。1960年4月8日,他和王翠霞的婚礼上,哈密县长带着维吾尔族乐师来道贺,都塔尔弹起《新疆好》,朱述道看着红地毯上的新娘,突然懂了“支边”的另一层意思:不光要开垦这里,更要安新家留在这里。
2004年,王翠霞骨折卧床,朱述道成了“全职护工”。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熬粥,温到不烫嘴才喂她。晚上坐在床边,给妻子读报纸上的新闻,就像年轻时在田埂上给她讲挖渠的趣事。“她一辈子跟着我吃苦,我得好好待她。”
2017年妻子走后,时年78岁的朱述道找出孩子们不用的作业本,戴着老花镜趴在桌上写回忆录。凌晨三四点,台灯还亮着,笔尖在纸上沙沙响,最多一天写了7000多字。写到和王翠霞第一次见面,眼泪滴在纸上,晕开了“漂亮”两个字。那本《峥嵘岁月恋深情》里,“她漂亮,能吃苦”这行字,墨迹晕了又干,像极了戈壁上反复起落的日头。
如今,朱述道的窗台下,还摆着当年挖渠用的铁锨,木柄被磨得发亮。
“新疆不是他乡,是埋了青春,也藏着情书的地方。”老人合上手稿,望向远处的田埂。这封写了六十六年的情书,读信人是新疆,也是漫过指尖的流年。(韩冰洁 王侯 张智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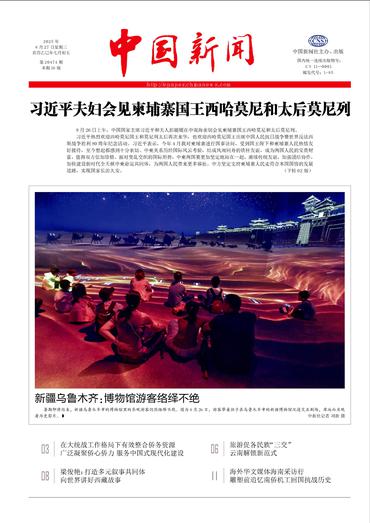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920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920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