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寻珍:老达玛沟出土克什米尔铜佛记
和田博物馆陈列着一尊来自策勒县老达玛沟遗址的克什米尔铜佛像。佛像面容安详,形态栩栩如生,仿佛以慈悲而明澈的目光温情注视着每一位来访者,传递着跨越千年的智慧与安宁。这尊铜佛像不仅是一件艺术珍品,更是文明交流的见证。它从何而来?又经历过怎样的时空旅程?其造型与工艺背后,隐藏着哪些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密码?

达玛沟佛教遗址的历史背景
“达玛沟”是“达摩沟”的同音异译,达玛沟的名称源自印度古代梵文“Dharma”(达摩),意为“佛法”或“智慧。”与古于阗语词缀“kho”(表示地点)结合,意为 “佛法汇集之地”。
作为于阗佛国故地,达玛沟保留了数量众多的佛教建筑遗迹。20世纪初,沿达玛沟水系从南到北先后发现了哈德里克、克科吉格代、巴拉瓦斯提、老达玛沟、乌尊塔提、喀拉沁、丹丹乌里克等佛寺遗址。21世纪新发现托普鲁克墩佛寺遗址群(小佛寺及2号、3号佛寺),喀拉卡勒干、喀拉墩、阿巴斯墩、托格拉克墩等佛寺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珍贵佛教文物。
老达玛沟遗址是和田地区一处重要的历史遗迹,是以老达玛沟为中心,周边分布着众多相邻的遗址点,共同构成了一片规模庞大、内涵丰富的古遗址群,历史年代为汉代至宋代时期。根据学者研究,这里可能对应历史上汉代的扜弥城、唐代的坎城以及明代的培因城。1929年,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教授在此考察后,推测其为《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的培因州。这些推测使得老达玛沟遗址的历史价值愈发重要。
克什米尔铜佛像的发现过程
老达玛沟遗址因多种原因废弃后,风沙肆虐,很快一座一座沙包侵袭了这里,昔日的家园被流沙覆盖。这片区域地下水位高,沙生植被生长茂盛,一丛一丛的红柳、梭梭等顽强地生长在沙包间,或延伸至沙包的半腰处、顶部,形成了独特的大漠景观。因为有适宜牛羊驼食用的植物,故放羊人经常在此放牧。
1989年秋天,策勒县达玛沟乡一个放羊的农民麦麦提明像往常一样,赶着羊群在村庄北部的沙漠地带放牧。这里沙包连绵起伏,骆驼刺、梭梭、红柳等沙生植被分布在沙包间,是放羊的好去处。羊群悠闲地啃食着骆驼刺的茎叶,缓慢地向前移动,不知不觉间闯入了老达玛沟区域。
在大漠中放羊的人是闲不住的,要么打柴火,要么放开嗓子唱歌解闷。麦麦提明卖力地在沙包上砍伐枯死的红柳枝,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储备柴火(现在已禁止砍伐沙漠植被)。突然间,他在沙包的底部发现了半掩的铜佛像,心中很惊喜,随即拨开沙土,小心翼翼地将佛像取了出来。这尊佛像呈古铜色,制造精美,佛像身上有多处锈色,底座上有几行不认识的文字。“发现宝贝了!”麦麦提明心中异常兴奋,他听人说,以前常有人在沙漠中寻宝,没想到自己也寻到宝贝了。他意识到,这尊铜佛是很珍贵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一定要上缴。很快,麦麦提明将这尊铜佛上缴到当时的和田地区文物管理所,文管所领导对他的行为高度赞赏,并按规定给予他现金奖励。
这尊铜佛像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它引发人们再次深入研究佛教传入于阗、于阗同克什米尔及吐蕃的文化艺术交流等方面的课题。
佛像特征与风格分析
老达玛沟遗址发现的这尊克什米尔造铜佛通高42厘米,底座宽25.5厘米、厚12厘米,现存和田博物馆。
造像特征:佛像跏趺坐于覆莲须弥座上,为如来形,黄铜铸造,头部圆浑,螺发、肉髻圆耸,椭圆脸型、宽额、双眉高挑,眼睑轮廓,眉间白毫及双眼嵌银,直视前方。颈部有三道纹褶,袒右肩式大衣,领口纹线细密,外缘饰折带纹。左手于胸前执大衣一角。下为方形束腰台座,正面刻梵文。
题记与年代:这尊佛像底座上有3行半梵文题记。长方形台座正面有前夏拉达字体(Proto-Śāradā)梵文题记。题记载明此像是由军官Dholaka及其妻子Narāyāsārvati、母亲Padmasukhā、儿子Amudasimgha、Punyasimgha和 Khukhethāla等共同施造供奉,年代大致在公元725年。
风格判定:从整体造型框架、风格样式和细部作法以及铜质等各方面分析,此尊铜佛像具有典型的克什米尔—吉尔吉特铸造特征,制作时间为公元7—8世纪,是一尊出自克什米尔的造像。
于阗与克什米尔、吐蕃的文化交流
历史背景:公元前1 世纪左右,佛教及佛教艺术沿丝绸之路传播到新疆,经南北两道分别形成了于阗、龟兹、高昌三个佛教中心,并与当地本土文化艺术相结合,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佛教造像艺术。
吐蕃人是生活在我国青藏高原的一个古代民族(即古藏族)。公元633年,松赞干布迁都逻些(今拉萨),建立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史料记载的地方政权——吐蕃王朝。吐蕃与唐朝在西域反复争夺,曾占据于阗,最终于866年因内乱退出西域。吐蕃占据于阗期间,采用羁縻制度,既保持于阗王族的政权,又在当地使用吐蕃的职官系统。此外,吐蕃在于阗推行了自身的军事和行政管理体制,并派驻大量驻军,于阗文和藏文是被共同使用的官方文字。
艺术交流:《于阗国授记》记载,吐蕃还在于阗建有寺院。藏文文献中还留下了于阗工匠在吐蕃进行艺术活动的记载。据藏族古典文献《拔协》记载,在松赞干布时就有于阗工匠在吐蕃从事造像活动,松赞干布还高度赞扬了一位来自于阗的工匠的精湛技艺,称他为“于阗派之王”。这位工匠有三个儿子,也同时在吐蕃帮助造像。《贤者喜宴》也记载,松赞干布在修建昌珠寺时,于阗工匠依其本地佛像样式塑造了菩萨的形象。《拔协》一书还记载,赤热巴巾建造宏伟的温江岛本尊寺时,也专门从于阗请来了著名的雕塑家李•觉白杰布。从这些记载可见,于阗对吐蕃佛像艺术的影响是真实存在的。吐蕃的于阗佛造像和于阗本地的佛造像应无太大的区别,我们完全可以从于阗同期佛造像作为参考,来研究和了解当时吐蕃佛像艺术中流行的于阗风格。
造像风格:于阗佛造像作为丝绸之路南道重要的佛教艺术遗存,其风格特征呈现显著的多元文化融合性。于阗佛造像大致的风格特征:它是一种复合型的艺术形式,在其造像上有犍陀罗、印度、波斯、粟特等多种艺术因素并存。其中,犍陀罗艺术因素给人的印象最明显,造像从躯体、衣纹,到台座都体现出犍陀罗艺术的遗风,同克什米尔金铜造像的风格类似。
传播路径与历史意义
地理脉络:克什米尔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群山环绕,地势高峻,在汉魏南北朝时期我国史书泛称此地为罽宾国,唐代称迦湿弥罗,唐高僧玄奘、悟空、慧超均到过此地。克什米尔北接西藏和新疆,西南为犍陀罗地区,东南为印度,地理位置正处在各种文化的交汇之处,可以说中亚文化的因素、南亚印度文化的因素乃至吐蕃文化的因素都能在克什米尔发现其痕迹。
克什米尔佛像头部浑圆,螺发密集圆缓,宽额,双耳垂肩;额间白毫扁圆而大,多以白银镶嵌;双眼嵌银,眼脸轮廓分明,眼神直视前方。克什米尔佛像也多发现于西藏地区,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近年西藏西部阿里地区也发现了数尊克什米尔佛及菩萨像,铜像多以黄铜铸造。上述这些特征与老达玛沟发现的克什米尔铜佛像是一致的。
传播路径:老达玛沟发现的克什米尔铜佛像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入和田地区的呢?专家学者研究推测,它很可能是通过汉代以来的罽宾道,进入塔里木盆地西南部的皮山而进入和田地区的。还有学者认为,这尊铜佛像在和田的出土是吐蕃占领和田时期,吐蕃军官及其眷属共同参与佛事活动的重要证明。
学术价值:老达玛沟发现的这尊克什米尔铜佛像很好地诠释了克什米尔对于吐蕃时期佛教传播的重要性,表明在克什米尔、吉尔吉特、于阗与西藏西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它不仅反映了于阗流行的佛教造像风貌,还揭示了于阗与毗邻的克什米尔和吐蕃王朝在佛像艺术上的密切关系。(居麦尼亚孜 郑宜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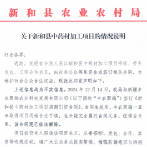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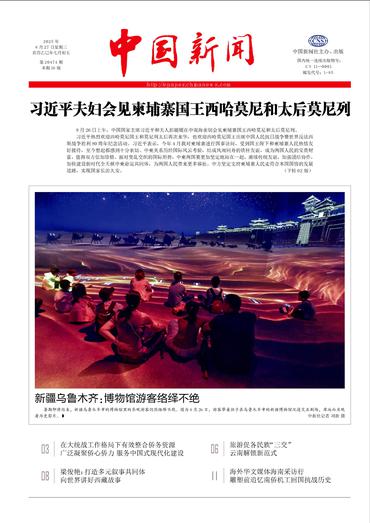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920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920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