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字无论走得再远,终究会回到克兰河畔——访哈萨克族青年作家巴燕·塔斯肯
“我的文字无论走得再远,终究会回到克兰河畔。”9月13日,在“我的家乡 我的亲人”——《克兰河畔》新书发布会结束后,青年作家巴燕·塔斯肯接受专访,分享了他跨越地域的创作初心、以河流为脉络的记忆书写,以及对故乡发展的深切期待,希望让更多人透过文字看见阿勒泰的多民族风情、自然之美与人文温度。

跨地创作:在广州的夜里遥思故乡
“在广州的夜里,我的思绪时常飘进克兰河畔的那片白桦树林,然后忍不住拿起笔。”谈及《克兰河畔》的创作,巴燕·塔斯肯的话语中满含对故乡的眷恋。这本书诞生于他在广州求学的岁月——并非刻意规划,更多是瞬间涌上心头的故乡记忆:童年在克兰河上游种地放牧的场景、和表妹埋葬小麻雀的温情、爷爷讲述的草原故事……这些碎片化的念想,被他一一记录在纸页之间。
“后来整理时发现,它们恰好能串联起我在阿勒泰的童年回忆,最终才有了《克兰河畔》。”巴燕·塔斯肯说,“大学时我偶尔写诗和短篇,现在回头看虽然稚嫩,但老师的鼓励给了我很大勇气——她说‘你的文字里有家乡的温度’,这句话我一直铭记至今。”从最初的零散记录,到后来投稿获得认可,他逐渐确信,“用文字讲述故乡故事”不仅能慰藉自己的乡愁,更能让远方的人触摸到阿勒泰的温度,这是一件值得坚持的事。
依河叙事:克兰河的流向串起童年回忆
《克兰河畔》的章节划分,蕴藏着巴燕・塔斯肯对故乡最细腻的情感寄托。“我们体内的血液,一半是母亲给的,一半是克兰河给的。”在他心中,克兰河是镌刻着童年、承载着乡愁的“生命之河”。
“克兰河上游”“水花”“阿勒泰的冬天”“山脚下”四个章节构成了童年最鲜活的底色。巴燕・塔斯肯回忆,童年在克兰河上游的诺改特村生活,村落沿河排开,家家户户的日子都与这条河紧密相连,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童年时我与爷爷奶奶的欢声笑语、邻里的互动,劳作、嬉戏的日常场景,都是克兰河边真实发生的事。克兰河不只是一条河,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联结民族团结、传递温情的纽带。”
“克兰河下游”则标志着他成长的转折——上初中后搬到下游市区,后来沿河流走向广州。章节依河的脉络划分,既按时间顺序,也以克兰河为线索,串联起童年记忆的轨迹。“故事里的人顺着不同的支流各自散去,读者跟着文字走,既能看到阿勒泰的四季之美,也能读懂我和故乡的羁绊。”
寄望故乡:山水与文化共护经济发展
谈起故乡的发展,巴燕·塔斯肯的语气中既有骄傲,也包含对“平衡”的思考。他坦言,每次回到阿勒泰,都能清晰感受到变化:拉斯特乡的村民告别旧村落,住进更便利的新居;凭借“人类滑雪起源地”的文化名片,冰雪旅游吸引国内外游客,古老毛皮滑雪板被广泛认可,为阿勒泰带来经济发展。这些变化让他由衷欣喜,但也更令他关注“发展背后的生态守护”。
“我在书里写过,小时候在山里捡到一粒金子,爷爷让我把它还给大山;奶奶看到有人大片采摘野菜、蘑菇时,总会上前叮嘱‘给土地留些生机’。”巴燕·塔斯肯说,“这些细节不是刻意渲染,而是阿勒泰人世代相传的生存智慧。我们的日子靠山水滋养,要是草原秃了、河水脏了,那失去的不只是风景,更是故乡的根。我们享受着山水的馈赠,更要把保护这片土地当成责任。”
他希望故乡的文化在发展中“扎稳根”。书中记载了阿勒泰人民对古老毛皮滑雪板的珍视、多民族共庆节日时的热闹场景。他说:“很多游客来体验冰雪项目、感受民族文化,希望大家能了解这些文化背后的故事。古老毛皮滑雪板是我们与自然相处的智慧;共庆节日是我们世代相传的包容与团结。”
“克兰河的水,不管流多远,最终还是会滋养这片土地。不管未来走到哪里,我的文字会朝着故乡的方向,在生活里体会,在回忆里书写。希望我的作品能让更多人看见阿勒泰鲜活的文化、多民族相处的温情;也希望远走他乡的阿勒泰人,能透过我的文字想起故乡的温度。”巴燕·塔斯肯说。(张楠 彭林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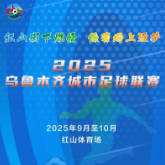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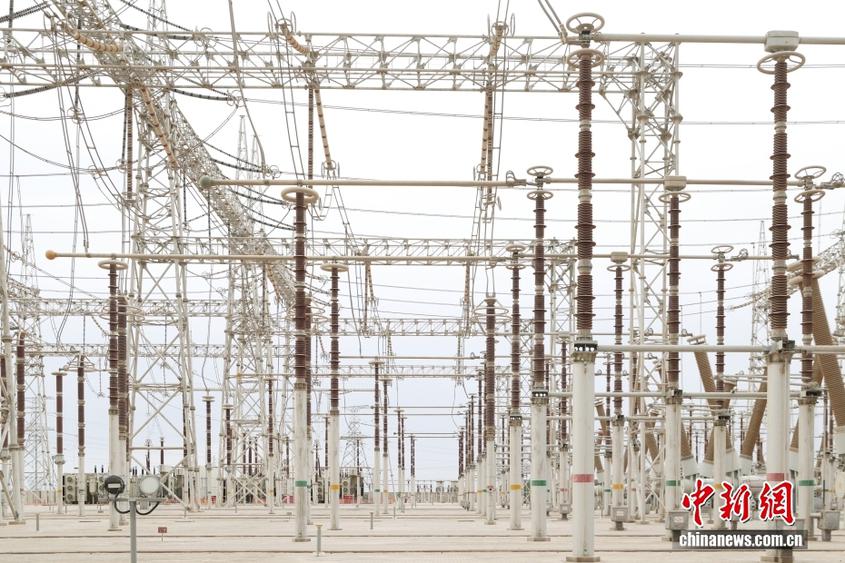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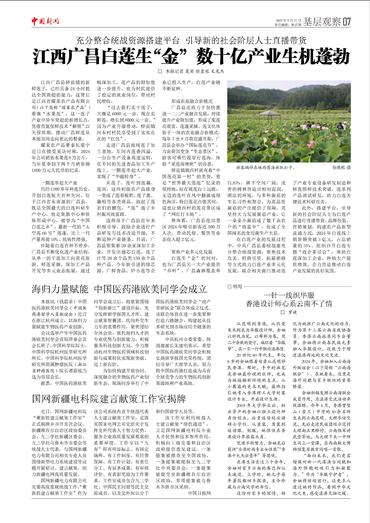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920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920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