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的两种轨迹
伊犁的午后,阳光斜斜切过单元楼的玻璃窗,在楼道里投下长长的光带。我牵着孩子的手往上走,三楼的防盗门虚掩着,母亲的笑声混着另一个熟悉的调子漫出来——是大哥,他从阿克苏回来探亲,比我们早到半小时。
“快进来!”母亲拉开门,鬓角的白在光里格外显眼。孩子侧身挤过去,鞋跟在木地板上敲出清脆的响,比去年又高了半头,进门时差点碰到门框。大哥从沙发上站起来,拍着孩子的胳膊笑:“几年没见,快认不出了。”
客厅茶几上,母亲泡好的茶在玻璃杯里漾着浅黄,枸杞浮浮沉沉。我们围着坐下,话头自然落到孩子身上。大哥说他这次开了十几个小时的车,路上总想起这孩子上大学四年,也就寒暑假能在家待一两个月。“等将来工作了,天南海北的,怕是一年到头,就指着春节能聚齐了。”
话音落下去,客厅里忽然静了。窗外的风卷着楼前的杨树叶,沙沙声从纱窗透进来。孩子拿起茶杯抿了一口,说:“大伯放心,我肯定常回来。”可我们都知道,这话轻得像羽毛,真到了那时候,隔着千山万水,“常回来”三个字,要费多少力气才能落地。母亲往孩子碗里夹了块肉,没说话,眼角的纹路却深了些。
我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总觉得日子漫长得过不完。放学回家喊一声“妈”,厨房就飘出饭菜香,从未想过有一天,见一面也要数着日历上的红圈。
“你跟他不一样。”母亲递给我一杯茶,目光落在我身上,“你每周都来,我这心里踏实。”
望着母亲鬓角的白,我忽然意识到,我和孩子正走着两条相反的路。他像被风扬起的蒲公英,越飞越远,把故乡缩成越来越小的一个点;而我正慢慢往回走,每周穿过熟悉的街道,踩着不变的时间点,把母亲的晚年走成一条安稳的线。
饭桌上,大哥给孩子夹菜,说着他小时候的糗事。孩子笑得前仰后合,眼角的纹路里还带着少年气,可那双手已经有了成年人的轮廓。我看着他,忽然懂了大哥没说出口的话——我们这代人爱孩子,和父母爱我们,原是同一种东西。只是父母那辈人,爱得更像白杨树,把根扎在原地,默默望着枝叶伸向远方;而我们,一边望着孩子的背影,一边往回走,替他们多守着些故乡的烟火。
临走时,孩子抱着母亲说再见,阳光把他们的影子叠在一起,一个长,一个短。我站在门边,看着大哥拍了拍孩子的后背,又转头朝我笑了笑。那笑容里有释然,也有了然——谁不是这样过来的呢?
下楼时,孩子忽然说:“老爸,其实我挺羡慕你的,每周都能来陪奶奶。”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等你将来有了自己的小家,就懂了。”
夜风带着点凉意,楼前的杨树还在沙沙响。我抬头看了看三楼的窗户,灯还亮着,想来母亲和大哥还在说话。忽然明白,所谓亲情,或许就是一场漫长的接力。父母把我们往前推,我们又望着孩子的方向,而那些回不去的时光,那些越来越少的相聚,其实都变成了心里的坐标,无论走多远,都知道原点在哪里。
就像我每周穿过几条街来看母亲,就像将来我或许会提着行李,去陌生的城市看孩子。时光在两条轨迹上流淌,一条往回,一条向前,却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紧紧系着。车开出小区时,孩子忽然说:“老爸,等到您以后退休了,就去我那儿住段时间吧。”
“好啊,”我说,“到时候,我跟着你走。”
风从车窗钻进来,带着伊犁特有的、混着尘土与阳光的味道。那些相反的轨迹,终究会在牵挂里,找到重合的温度。(蔡罗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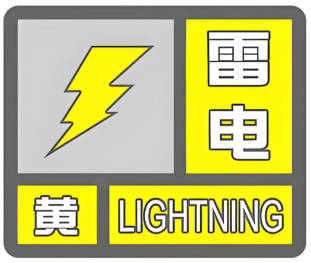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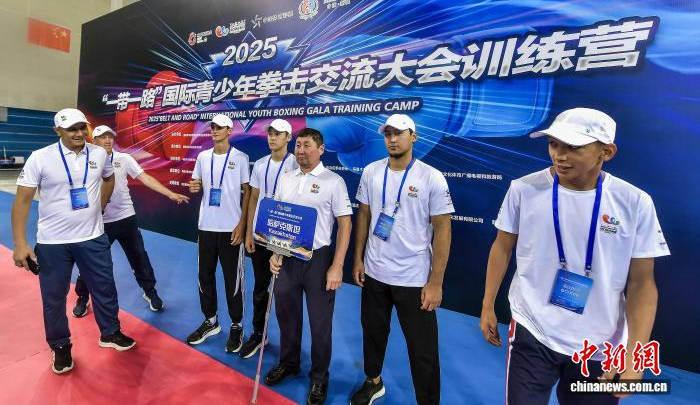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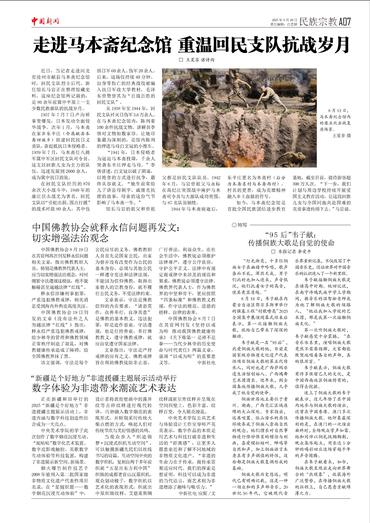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9201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9201号